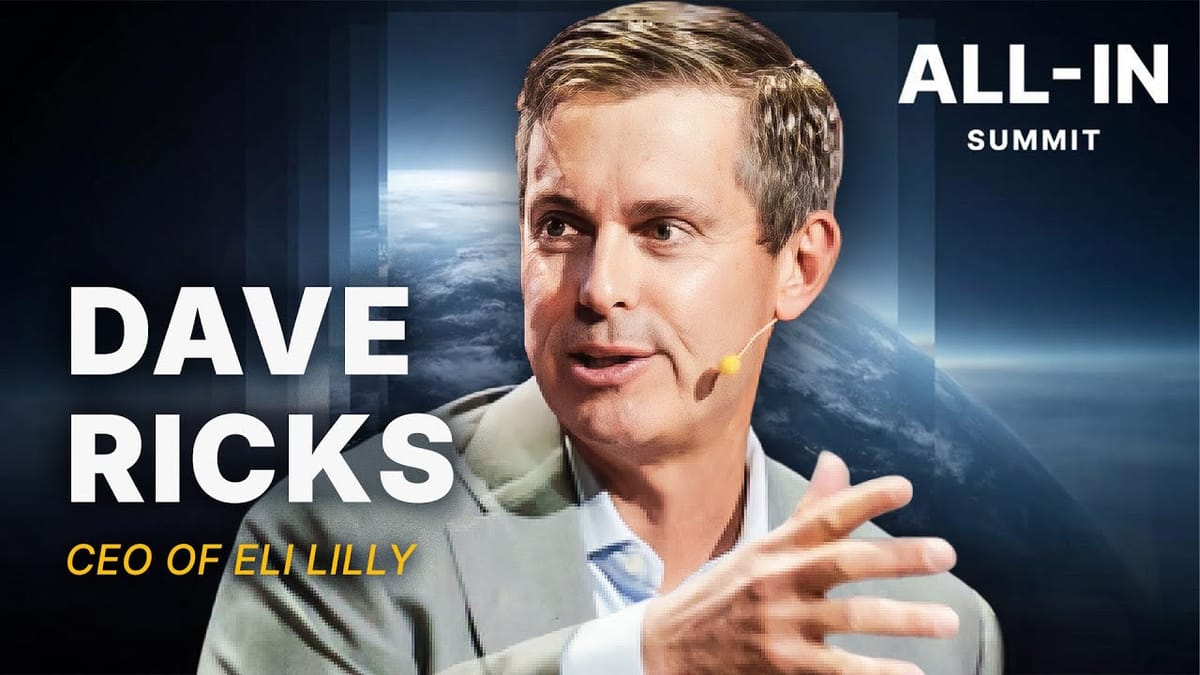這是一場堪稱製藥業近年來最坦誠、也最關鍵的公開對話。當全球市值最高的製藥公司 Eli Lilly 的執行長 Dave Ricks 坐上科技圈最火的播客節目《All-In Podcast》時,這不僅僅是一次企業宣傳,而是一場關於科學、商業倫理與人類未來的深度碰撞。特別的是,主持人本身就是藥物的使用者,他們的親身經歷與尖銳提問,讓這場對話跳脫了公關稿的框架,直擊這場「GLP-1 淘金熱」的核心。
一、 「食物噪音」的消失:不只是減重,更是心靈的解放
訪談一開始,主持人 Jason Calacanis 就拋出了一枚震撼彈,他直接向 Dave Ricks 致謝:「你的藥物改變了我的人生。」Calacanis 分享自己從 213 磅減到 172 磅,但他強調,這遠不止是體重數字的變化。
他創造了一個後來被廣泛引用的詞彙——「食物噪音」(Food Noise)。
「我過去的人生中,大腦裡總是有個聲音在喋喋不休地談論食物。下一餐吃什麼?我餓了嗎?那個披薩看起來真好吃……這種噪音從未停止。而 Mounjaro 做的最神奇的事,就是讓這個聲音徹底消失了。我第一次感覺到,原來這不是意志力的問題,而是生理機制的枷鎖。」– Jason Calacanis 形容道
這個概念瞬間點燃了討論。它將肥胖從一個「缺乏自制力」的道德批判,重新定義為一個由生理訊號主導的醫學問題。這種從使用者第一視角出發的見證,生動解釋了 GLP-1 藥物為何具有革命性:它不僅是讓人吃得更少,更是從根本上修復了使用者與食物之間的關係,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「心靈平靜」與自由。
二、 二十年的豪賭:GLP-1 如何從糖尿病配角走向減重巨星
許多人以為 Mounjaro 和 Zepbound 是一夜成名的奇蹟,但 Dave Ricks 澄清,這是一場持續了近二十年、投入數百億美元的漫長豪賭。他還原了這段驚心動魄的研發史:
- 卑微的起點:Eli Lilly 最早的 GLP-1 藥物 Byetta 於 2006 年問世,當時是一款每日需注射兩次的糖尿病藥。減重?那只是財報中一個不起眼的副作用。Ricks 回憶道:「2007 年的年度報告封面是一位女士說:『我的糖尿病得到控制,而且我也減了一點體重。』沒人預料到這句話背後蘊藏的巨大潛力。」
- 「意外」的轉捩點:真正的突破來自於雙重作用劑 Tirzepatide(Mounjaro/Zepbound 的活性成分),它同時作用於 GLP-1 和 GIP 這兩種腸泌素受體。Ricks 分享了一個決定性的內部故事:在新加坡進行的一項針對健康男性的早期臨床試驗中,研究團隊發現受試者的體重下降得又快又多,遠超預期,以至於他們不得不緊急中止試驗,因為效果「太好了」。
那個「意外」的結果,成為 Eli Lilly 的「尤里卡時刻」。團隊意識到,他們手中的可能不僅是一款更好的糖尿病藥,而是一款能夠改寫肥胖治療史的革命性藥物。這也證明了,偉大的科學突破,往往來自於長期的堅持、敏銳的觀察以及在關鍵時刻敢於加倍下注的勇氣。
三、 每月一千美元的針劑:創新、利潤與道德的激烈交鋒
對話中最尖銳的環節,無疑是關於定價的辯論。主持人直言不諱地質疑,Eli Lilly 賺取了巨額利潤,為何不降低價格,讓這款改變人生的藥物惠及更多人?
Dave Ricks 並未迴避,而是系統性地闡述了製藥業的商業邏輯與困境:
- 創新的燃料:他強調,高昂的定價是為了回收天文數字般的研發成本(Eli Lilly 今年將投入 142 億美元),更重要的是,為下一代藥物的開發提供資金。他發出警告:「如果你把價格砍掉 80%,你實際上是扼殺了整個行業的創新引擎(you snuff out the innovation engine)。那些等待阿茲海默症、癌症新療法的患者,將是最終的受害者。」
- 價格下降的承諾:儘管捍衛定價,Ricks 也承諾會透過折扣計畫降低患者的自付費用,並預期藥物價格會以「個位數的年通縮率」(single-digit deflation)逐年下降。他特別提到,即將推出的口服劑型將是降低生產成本和終端價格的關鍵一步。
- 真正的敵人是體制:Ricks 認為,核心問題在於保險體系。他反問道:「為什麼我們願意為治療高血壓、高膽固醇的藥物買單,卻不願意將肥胖視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並納入保險給付?」他的目標是推動整個醫療體系承認肥胖的疾病屬性,讓保險公司承擔主要費用。
這段交鋒揭示了在救命的藥物背後,創新、利潤與可及性之間永恆的緊張關係。
四、 意外的驚喜:從戒酒、戒賭到治療憂鬱症的潛力
如果說減重是 GLP-1 的主旋律,那麼它對大腦的影響,則是這場訪談中最令人興奮的未來篇章。無數使用者回饋,這類藥物似乎抑制了各種「渴望」,其影響遠遠超出了食物:
- 物質成癮:減少對酒精、尼古丁的渴求。
- 行為成癮:降低賭博、購物甚至咬指甲的衝動。
Ricks 證實,這些傳聞並非空穴來風。他透露,Eli Lilly 正在利用一款對大腦活性影響更大、但減重效果稍弱的新型 GLP-1 藥物,正式啟動針對躁鬱症(Bipolar Disorder)和重度憂鬱症(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)的臨床研究。
這個消息意義非凡。如果 GLP-1 藥物真的能透過調節大腦的獎勵中樞來治療精神疾病,這將是自百憂解(Prozac)問世以來,精神病學領域最重大的突破,可能為全球數億患者帶來全新的希望。
五、 淘金熱的陣痛:供應鏈、灰色市場與破碎的醫療體系
需求如海嘯般湧來,Eli Lilly 正面臨巨大的營運壓力。
- 瘋狂擴產:為了應對全球性的藥物短缺,Ricks 透露公司正在美國建造 6 座新工廠,並計劃在未來六個月內再宣布 4 座。這是一場史詩級的產能競賽。
- 灰色市場的警鐘:主持人提到了來自中國等地的複方藥(Compounding)和未經授權的仿製藥。Ricks 嚴肅警告,這些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毫無保障,「你根本不知道你往自己身體裡注射的是什麼」,呼籲使用者切勿冒險。
- 對體系的尖銳反思:
- PBMs(藥品福利管理機構):Ricks 毫不客氣地批評 PBMs 這個中間商已經「走到了其生命週期的盡頭」,其商業模式已從為客戶省錢,演變成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抽成機器。
- DTC 廣告(直接面對消費者廣告):最令人意外的是,Ricks 表示他支持減少藥品電視廣告。他認為現行法規過時,導致廣告充斥著令人困惑的副作用清單,不如將資源投入到能真正教育患者的管道。
六、 下一個聖杯:大腦
訪談結尾,主持人問道:「繼 GLP-1 之後,下一個同等級的重大突破會在哪裡?」
Dave Ricks 的回答沒有絲毫猶豫:「大腦疾病(Brain Disease)。」
他解釋說:「從阿茲海默症、失智症到憂鬱症和焦慮症,這些疾病是造成人類痛苦、折磨和經濟負擔最主要的根源,而我們現有的工具卻少得可憐。這條路異常艱難,但這正是我們未來希望攻克的方向。」
這不僅揭示了 Eli Lilly 的長期戰略,也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充滿希望的未來藍圖:當我們開始解開大腦的奧秘時,我們將不僅能治癒身體的疾病,更能撫慰心靈的創傷。